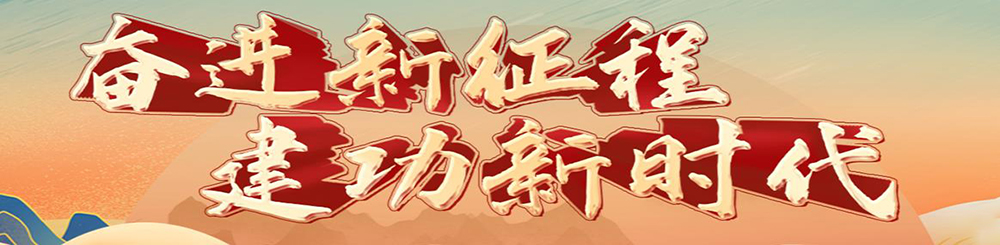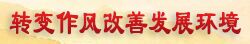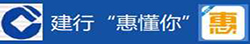民族管弦樂(lè)《大河之北》:張千一的人文氣質(zhì)
編輯:魏少梧 信息來(lái)源: 西e網(wǎng)-光明網(wǎng)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19-1-9
民族管弦樂(lè)《大河之北》的人文氣質(zhì)
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民樂(lè)創(chuàng)作在經(jīng)歷了一個(gè)世紀(jì)的借鑒與改良之后,正逐漸收回“西望”的目光,在重新審視自身傳統(tǒng)的蛻變中確立起一種新的品格。作為中國(guó)文化特有的聲音符號(hào),如何在保有傳統(tǒng)音樂(lè)美學(xué)神韻的基礎(chǔ)上,跳脫原有的地域化、民間化的文化語(yǔ)境,使其成為記錄當(dāng)代國(guó)人情感與精神風(fēng)貌的一種具有現(xiàn)代意涵的世界性話(huà)語(yǔ),依然是當(dāng)代音樂(lè)家不斷追尋的課題。在這方面,張千一的新作《大河之北》或能為我們帶來(lái)一些啟示。
一位作曲家成功的標(biāo)志之一,就是在多年的藝術(shù)淬煉中形成自己獨(dú)有的風(fēng)格。它或顯現(xiàn)于個(gè)性化的音樂(lè)語(yǔ)匯、偏愛(ài)的體裁題材,或隱含于獨(dú)特的文化訴求、美學(xué)意韻當(dāng)中,成為我們解讀其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的“關(guān)鍵詞”。屬于張千一的關(guān)鍵詞之一,當(dāng)是“言簡(jiǎn)意賅”——他善于通過(guò)高度凝練、耐人尋味的語(yǔ)匯來(lái)塑造個(gè)性鮮明的音樂(lè)形象。如寫(xiě)意山水,寥寥數(shù)筆,意韻自在;又如五絕七律,短小精煉,回味無(wú)窮。
《大河之北》便是這一風(fēng)格的典型代表。開(kāi)篇第一樂(lè)章《士——燕趙悲歌》,作曲家并沒(méi)有使用固有的音樂(lè)素材來(lái)彰顯河北特色,而是運(yùn)用自由十二音技法,創(chuàng)作了一個(gè)戲劇性主題。透過(guò)充滿(mǎn)現(xiàn)代感的音響,刻畫(huà)出燕趙大地慷慨悲壯的文化底蘊(yùn),從而為整部作品涂抹上厚重的歷史人文色彩。第四樂(lè)章《大平原》堪稱(chēng)現(xiàn)代氣息與民族風(fēng)味巧妙融合的典范。透過(guò)這一樂(lè)章的主題寫(xiě)作,我們?cè)俅胃惺艿阶髑腋叱囊魳?lè)造型功力——通過(guò)調(diào)式交替的手法,為一個(gè)徵調(diào)式音階注入新的色彩,在不斷變換的光影色調(diào)中,將大平原的寬廣遼闊一覽無(wú)余地展現(xiàn)在人們面前。雖然類(lèi)似手法在中外作品中并不鮮見(jiàn),但張千一在音樂(lè)中所營(yíng)造的飛機(jī)航拍似的翱翔和鳥(niǎo)瞰,卻是只有沐浴在現(xiàn)代文明中的人們才能領(lǐng)略到的動(dòng)感與開(kāi)闊。
《大河之北》對(duì)于民俗性段落、地域文化符號(hào)的詮釋?zhuān)瑯颖憩F(xiàn)出充滿(mǎn)藝術(shù)性、趣味性的想象空間。如第二樂(lè)章《趙州橋隨想》(二胡與樂(lè)隊(duì))中,作曲家不僅通過(guò)拱形曲式結(jié)構(gòu)來(lái)表達(dá)“橋”的意象,還將《小放?!贰端牧洹愤@兩首同為表現(xiàn)趙州橋但音樂(lè)性格相異的民歌并置使用,以增加音樂(lè)的色彩對(duì)比。同樣的思路延續(xù)到了第三樂(lè)章《回娘家》(吹打樂(lè))、第六樂(lè)章《避暑山莊——普陀宗乘》中。這些傳統(tǒng)的音調(diào)擴(kuò)展與疊加,增加了音樂(lè)可聽(tīng)性,也從敘事上拓展了民間音樂(lè)素材內(nèi)容表達(dá)上的單一性,使聽(tīng)者獲得似曾相識(shí)又出乎意料的欣賞體驗(yàn)。
除了音樂(lè)細(xì)節(jié)上的匠心獨(dú)運(yùn),作者在民族管弦樂(lè)隊(duì)的整體音響表達(dá)上同樣做出了諸多思考和嘗試。對(duì)于借鑒西方管弦樂(lè)隊(duì)結(jié)構(gòu)組建的現(xiàn)代民樂(lè)隊(duì)在表現(xiàn)力上的優(yōu)劣特點(diǎn),張千一顯然有著深刻而清晰的認(rèn)識(shí)。因此,《大河之北》中,他充分運(yùn)用了規(guī)避與兼顧的原則——將音樂(lè)性格近似的樂(lè)器分組使用,讓音響存在沖突的樂(lè)器交替陳述,利用不同音區(qū)、不同語(yǔ)匯營(yíng)造音樂(lè)上的對(duì)比,等等。通過(guò)這些手法,有效地規(guī)避了民族管弦樂(lè)隊(duì)在音響上“不和諧”“不均衡”的問(wèn)題,在凸顯樂(lè)曲交響性的同時(shí),盡可能發(fā)揮每種樂(lè)器、每個(gè)聲部的個(gè)性特色。
真正具有深度的作品,除了給人以聽(tīng)覺(jué)審美的愉悅和享受,更能引領(lǐng)人們進(jìn)入另一個(gè)思想維度,對(duì)作品表達(dá)的文化內(nèi)涵展開(kāi)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和思考。張千一沒(méi)有從地域的概念上去詮釋“河北文化”的諸多方面,而是以一種富于歷史縱深感的、開(kāi)放包容的文化觀(guān)去挖掘它的多重內(nèi)涵。第七樂(lè)章《關(guān)里關(guān)外塞外》中,作者有意將河北民歌《放風(fēng)箏》、東北民歌《正對(duì)花》以及蒙古族音樂(lè)素材熔于一爐,彰顯出河北地處北方多地域文化交匯點(diǎn)上的、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質(zhì),為整部交響樂(lè)畫(huà)上一個(gè)更加開(kāi)放的句號(hào)。
近年來(lái),中國(guó)的民族器樂(lè)創(chuàng)作呈現(xiàn)出多元發(fā)展的態(tài)勢(shì)。有的選擇向外擴(kuò)張,通過(guò)與其他姊妹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空間的疊加為民樂(lè)發(fā)展開(kāi)拓出新的場(chǎng)域,如近來(lái)風(fēng)行一時(shí)的“民族器樂(lè)劇”;有的選擇揚(yáng)長(zhǎng)避短,另辟蹊徑,充分張揚(yáng)民族樂(lè)器在藝術(shù)和文化表現(xiàn)力上的個(gè)性,如當(dāng)前以“學(xué)院派”為代表的方興未艾的民族室內(nèi)樂(lè)創(chuàng)作;還有一種就是選擇立足原地,繼續(xù)深挖,在現(xiàn)有的表現(xiàn)范式中探求更多的可能性。張千一的《大河之北》正是最后一種方向的代表。以往的同類(lèi)題材作品,多是利用專(zhuān)業(yè)作曲技法對(duì)地方音樂(lè)素材進(jìn)行再加工。而這部由七樂(lè)章連綴而成的民族交響詩(shī)畫(huà),通過(guò)對(duì)這塊土地歷史文化的回望與沉思、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的描摹與刻畫(huà)、燕趙文化之精神氣質(zhì)的塑造與解讀,使作品從形式到內(nèi)容都彰顯出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文氣質(zhì)。
(作者為《人民音樂(lè)》雜志副主編)
張萌
原文鏈接:http://reader.gmw.cn/2019-01/03/content_32289729.htm
下一篇:
熱門(mén)資訊